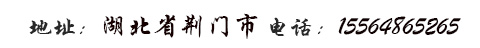蔡芳本蓝鲸诗传
|
蓝鲸诗传 作者:蔡芳本 一 一路走来,蓝鲸走走停停,时断时续,虽没有什么丰功伟绩,也算固守了一方疆域,在诗歌的海洋上平安地遨游。 蓝鲸的诗人们一代一代,代代相传,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,不想大富大贵,大红大紫,只想平平安安地将诗歌的事业进行到底。蓝鲸的诗人们从心底里热爱诗歌,热爱诗歌的事业,默默地写,默默地做,不去攀比,不去显耀,只想将诗的根在晋江的大海上扎得更加深远。 与往期一样,翻开本期的《蓝鲸诗刊》,依然云蒸霞蔚,依然气象万千,真纯的诗歌依然翻腾在诗歌的海洋中。老诗人保持不变的品格,还没被新生的潮流淹灭。古老的题材,传统的写法,丝毫不会褪去诗歌的颜色。蔡桂章的一首《清明》,情真意切,声声呼唤,儿女情长,催人泪下。一贯煽情的蔡桂章,现在的手法跟过去几无二致,在多元化的今天,他能有这样的坚守,无疑值得肯定。诗歌需要创新,但创新不是诗歌的全部。诗歌的全部在于诗歌的本质。诗歌的本质在于能否感动人,能否撼动人,能否挑动人,能否惊动人。按照诗学家陈仲义的解释,感动基于情感,这是最原始的衡量诗歌的标准。情感的原素是信仰,是仁爱,是忧患,是担待、使命、责任和正义。情感是一切的基础。蔡桂章的所有诗歌就是这一基础最良好的体现,并且常写常青。希梅内斯说过一句话:"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,正是凭借着感情,我们才居住在这世界上。"蔡桂章正用酸涩的泪水,滋润我们日渐枯萎的乡情,让我们更加诗意地居住在这世界上。 旅京的诗人王永志,旅粤的诗人桂汉标,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蓝鲸诗人,但他们却与蔡桂章一样,都有一颗不老的心。几十年来,他们跟蓝鲸的关系若即若离,诗心却是一致的。这次他们加入《蓝鲸诗刊》,不能不说是蓝鲸的一种荣誉。王永志的诗,平实直朴,传统味强,他比蔡桂章更有一些理性的肌理。一样写乡土,蔡桂章用的是感觉,王永志用的是判断和理解。而桂汉标先生掺入的更多实新鲜的当代的语言,所写的东西也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时尚现象。桂汉标先生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乡土,是裂变中的乡土。这种乡土"创造快乐,因为爱而出彩","时尚的大海啊正波浪翻浪涌,""万水千山总是情","但愿声光电不再互撕互咬/未来该是彩练当空舞。"蔡桂章是过去的乡土,王永志是即目的乡土,桂汉标先生是现在时将来时的乡土。老一辈的乡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体系。三种乡土互为补充,互为表里,“山川如画,一一收入镜头/生活如诗,行履处处炫彩”(桂汉标《新客家》)这就是老一辈蓝鲸人的魅力所在。 洪安和、王荣挺们更是一以贯之,坚持不变的风格。虽然洪安和有个时间段游离了鲸群,但这些蓝鲸诗人不会随波逐流,不会随风摇摆,他们沉潜在诗歌的海洋下面,去实现自己的主见。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,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操作主张。他们善用的修辞手法,抵达了精神的自由境界,并为这种精神建立了一个牢固的支点。现在,他们告别了青春时期的喃喃自语,表现出更多的叙述与描写或者思辨特征,从而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。 下一代的蓝鲸人也并没有走多远,他们也在前人的航道上踽踽徐行。只不过,他们更不甘心于墨守成规,他们一向具有创造革新意识。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,他们的思想决不保守,在现在的中国,他们几乎是栋梁之材。在诗的领域,他们占据大半个江山,曾一度引领诗坛。蓝鲸的诗人像吴世泽、像施勇猛,他们曾经举着诗歌的旗帜,横冲直撞,奇招怪出连篇累牍。他们企图颠覆传统的诗歌形式,让诗走向一条全新的路途。但他们好像没有足够的体力,没有足够的能量储备,没有清醒的认识,他们凭着无畏的青春勇气,却没有足够的定力,也不能够专心一致,致使他们的行为显得有些盲目,如果没有这种盲目,他们想要攻城略地,想要开辟新航道,都不是臆想天开的事。 现在我看到的是吴世泽似乎从狂热中回归,从天空中落地。一段时间以来,吴世泽一反常态,一直写一些凝重的诗,写一些直抒胸臆的诗。这首诗不仅感情真挚,饱满,深沉,还开阔大气。这一期《蓝鲸诗刊》上吴世泽的诗太不像过去的吴世泽了。他的这首诗脉络清晰,语言节奏感强烈,也是陈仲义先生讲的那种能撼动人的诗,简直是蔡桂章的翻版。所不同的是,蔡桂章轻灵,而吴世泽凝重。吴世泽写这样的诗是显示他心态的老练,还是显示他处世的成熟呢?不太明白。有人又说,这首诗颇有20世纪先锋诗人的味道,是不是说,吴世泽跟21世纪没半毛钱关系呢?而真正的答案是,吴世泽20世纪就走在21世纪的路上。 那么,我们看一下施勇猛。施勇猛一直将时间取出来,放在诗歌的肩上打磨。他完全可以属于21世纪。他没有变。如果有变,那也只能说,他不再一泻千里,他变得内敛一些,变得含蓄一些,完整一些。过去,他的诗没开头,没结尾。他在开头处添上多少行都是开头,在结尾处添上多少行都是结尾,诗歌成了他倾泻语言的地方。从目前的诗歌看,他开头是开头,结尾是结尾,完全是有头有脸的一种结构方式。他离开了散漫无序的操作方式,将诗歌改变得十分规矩,这好像又是一种传统的复归,只是施勇猛本身没有意识到而已。施勇猛是“一个人醒着/一个人做梦/不在旧时光/不在新世界”,他想要的“都是灰”,因为“为我取名的/终将取走我的名字”。施勇猛很了然地看清一切,但是他又有点担心,他的诗歌现在处在一个复杂的时刻,他到底要跨到哪一个疆域? 比施勇猛稍晚些的蔡长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,但他跟施勇猛走得好像不是一条道。蔡长兴的诗歌很是煽情。他将生活中的事物写得格外饱满,实实在在,有血有肉,有痛感,有质感,能让读诗的人鼻子一酸,眼泪流出。显然,蔡长兴不是先锋一族,他还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。他跟蔡桂章不同的是,在遣词造句方面他更有现代人的感觉。蔡长兴也在探讨,也在求索更适合他的诗歌道路。 对于这个问题,这一代的蓝鲸妹妹们是不值一提的。蓝鲸的姐姐妹妹们陈榕宜、许燕影、洪雅清、蔡白萍,甚至连曾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,现在又突然华彩出现的蔡晓芳,都一如既往地走美丽纯情路线。有时化淡妆,有时素面朝天,都是本色出场。“只一个转身/就倾倒半个江南”(蔡晓芳《如同从我身体里出逃的诗情画意》)。真想不明白,从她们身体里出逃的怎么都是诗情画意呢?她们也要油盐酱醋茶,也要吃喝拉撒睡,可是她们的表现就是那么小资,那么优雅,那么美。她们怎么就那般诗意?这些女诗人代表着蓝鲸的一种势力,一种方向。甚至连稍后些的骆锦恋,林娜,都是这样一种品质。“要命的秀气,盛满我的春天/弯腰或者转身,都有诗的模样/除了吹风,我什么都不想/这辽阔的时光,把我的孤单/吹向所有的花开。”(林娜《一个人去看花》)一个人去看花,干吗不两个人去,真要了我们的命,当然不会要了诗歌的命。这些女诗人都有这样的本领,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搔首弄姿,在平常中找到美丽之处。可以肯定,她们这样写诗,一百年不会变。 还好,有人想变。至少张美娜这个坏女孩想变。这个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坏女孩,本来也不属于诗的胚种,她虽然有诗的气质,但她没有女诗人的模样。她偶然写诗也不成体统,写好一首诗真要令人刮目相看了。本期《蓝鲸诗刊》上的几首诗,是一个列外,也算是别开生面了。一样写爱情,她不会写得像细雨像微风,缠缠绵绵;不会像写棉花,绵绵软软。她写爱情写得像钢铁,铮铮作响,像革命烈士的就义诗篇。她很大胆很直白,没有任余商量余地,也不叫你回味,她大声宣称“请不要向这是为什么/自古爱情都是这副模样”。这是他散文的风格。她的散文就是这样直率这样尖刻。真不要命啊,林娜要了我们的命,一个张美娜也来要我们的命。林娜用得是软刷子,张美娜用的是大砍刀,杀将而来。好在诗歌的心胸十分宽大,可以容纳柔情蜜意的姿态,也可以接洽凶巴巴的样子。不然,这个女人那么凶,怎么能应付得了。蓝鲸的这些女人真是要命的人哪。张美娜这个不写诗的诗人,这样大刀阔斧地杀出,实际上也是为蓝鲸放出一个信号:蓝鲸女人们的诗歌眼线可以割得更开阔一些,手法可以更多样一些,表现可以更大胆一些。那种闺房式的、怨妇式的、自恋式的内容是否可以少一点,是不是可以像张美娜写的:“用方天画戟划出红色区域的势力范围进行爱情掠夺”! 遗憾的是,后起的几个小姑娘,似乎是刚出道的原因,还是没有勇气,小心翼翼,循规蹈矩,亦步亦趋,不能开辟一条新的路径。她们依然写得很美,很纯情,但她们不能使人眼前一亮。这真有点很令人可惜。 二 晋江的文学现象很有意思,什么文学品种都掺杂在一起,许多人扮演反串的角色。写小说的来写诗,写诗的也来写小说;写散文的也写诗,写诗的也写散文;摄影的也来写诗,写诗的也去摄影。什么时候叫谁扮演什么就扮演什么,什么时候该出场就出场。甚至,有太多时候,他们都会按捺不住,自己踊跃出场,主动来一个满汉全席,来一场群鲸闹海。 这一次出场的李相华应该是个代表人物。李相华的小说相当出彩,因为有了李相华,晋江才可以跟人家谈小说(许谋清不算,他是京城的人),李相华为晋江小说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李相华也写诗(跟黄良一样,奇怪他这次没出面,他可能将位置传给他儿子黄子午了)。李相华的诗写得跟小说一样,有情节有故事,但绝对有诗的内核。他在故事中蕴含诗意,这是一种需要慢慢品味的诗意,不是扑面而来的诗味。这种味道不甜不腻不呛,只有在岁月的深处才能找得出来,闻得出来。这也给蓝鲸诗歌指出了诗歌的另一种可能:不是貌似诗歌才是诗歌,有时不像诗歌的反而是诗歌。这一种诗歌就是陈仲义所讲的撼动。撼动,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蒙。是一种启迪、启示,或者让人有一种深思,一种反省。撼动是从心灵深处的挖掘,是让你长久留在心底的后座力。李相华的诗,可以说是炮炮打响,虽然产量不高,但都有份量,都是精品。 刚才提开的黄子午,他严格意义上也不是诗人,他是摄影家。他鬼灵精怪地拍出各种时尚小电影,迷惑你的双眼,改变你的观念。他跟他老爸不同。他老爸接的是古旧乡土的血脉,他连接的是现代都市的地气。他赶在陨石落地时,送文件,送快递。按下按钮,寻找生机。多么爽快的语言,多么现代的意识,这才是21世纪90年代人的气质。黄子午的诗节奏感很强,而且是快节奏,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乐拍,他的诗也很短,干净利落,并且他的跳跃性很强,思接千载,落地生根。他以一个摄影家的镜头解释这个世界。在这个时代,在蓝鲸这个群体里,他无疑是可以游得更远的一条小鲸。 而那些写散文写小说的蓝鲸们呢?林火烟、王东雄、李伟才等等,他们也在努力以一个诗人的本质出现。林火烟《山高皇帝远》,其实离诗歌很近,他的诗在打造一个古老的氛围。他也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,由“小说想到诗歌,触痛到生死情结。”李伟才则在散文笔法的散文诗中“尽情释放对美、对恶、对厌、对喜、对烦的演绎。”不得不说,李伟才是个好同志,他是个泛爱主义者,凡文艺的东西什么他都爱,爱文学,爱艺术。琴棋书画文无所不爱无所不精,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!“已然可以自由玩乾坤,这是多么幸福的领悟。” 高人啊! 三 最后,不能不提到蓝鲸的老将而且是主要骨干主要引航者的吴谨程、颜长江、安安、刘志峰、吴明哲。这五虎大将对蓝鲸不离不弃(除吴明哲稍微转移视线外),才能使蓝鲸在今天依然乘风破浪,才使得蓝鲸的队伍日益壮大,后继有人。 这五员大将诗风几乎不变,诗心自然不改。他们是诗歌的风向标,是蓝鲸诗歌的掌舵人。他们应该是令人敬佩的人。他们向诗歌致敬,诗歌也向他们致敬。 吴谨程是大海的诗人,除了他的代表作《大海啊,我永生永世的爱情》之外,吴谨程写了各种题材的诗,基本上是汹涌澎湃,大气蓬勃。颜长江以一以贯之的严肃,书写乡土,铸造《丰碑》,“为民族铸魂”。安安则在依旧充满禅味的同时,将生活的气息注入其中。他当然的委婉,当然的含蓄中也有社会的责任与担当,他跳出了禅门之外去迎纳现实的社会,甚至迎纳政治。在《你是我的月娘》这组诗中体现得非常充分。这就说明安安是一个善于接纳新事物的人,他并不保守,而是心胸开放,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。一个诗人不能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人,安安从他的诗中告诉我们这样的经验。 刘志峰似乎很久没写诗了,但是他对诗歌表现出的持久的热烈的执着却是什么人都不能比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可以没有蓝鲸,但不能没有刘志峰。没有蓝鲸,可以有白鲸,而没有刘志峰,诗歌谁来保护,谁来扶持?虽然,近些年刘志峰编辑了各种各样的书籍,使他更向编辑家靠拢,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本质上的一个诗人存在。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,刘志峰也是诗歌的使者。应该这样说,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不是诗人,不是诗歌,而是诗歌的使者。 作者简介:蔡芳本,笔名老山羊、郑闲,福建泉州人,晋江市蓝鲸诗社总策划、创始人之一。年毕业于福建师大中文系。毕业后分别在师专、中专、中学任教。年转入《泉州晚报》任编辑。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诗集《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》、《逆飞的荆棘鸟》、《只有你的声音》,散文诗集《紫丁花香》,诗书影集《故乡屋檐下》,散文随笔集《过简单生活》、《做一只快乐的猪》。现任泉州七彩艺文会馆馆长、泉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 福建省晋江市蓝鲸诗社成立于年3月12日,由晋江市“第四代”诗歌作者联合发起组建。28年来不断发展,成为享誉诗坛的“晋江诗群”。诗社中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0人、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70人,队伍之大居全省县(市、区)首位。 “晋江诗群”在国内文坛迅速崛起。晋江市主办的文学报刊《星光》、《蓝鲸诗刊》颇为社会各界北京中科医院好不好有人去过北京中科医院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lanjinga.com/ljsyxh/54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上海爸妈警惕了又一种游戏在青少年中偷偷
- 下一篇文章: 你知道吗青少年身上有这种标识一定制止